【ppzhan摘要】隨著科技的進步,行業新技術總是應勢而生。數字出版已經成為出版行業的主要趨勢。出版和印刷在傳承人類文明、傳播知識信息上起著重要作用,數字技術的出現對傳統出版提出了挑戰,使用電子閱讀器也對傳統的紙質印刷提出了挑戰,主動應對挑戰應該是出版與印刷業的共同職責。
數字技術稱得上是二十世紀的偉大發明,數字技術的出現改變了信息傳遞;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改變了生產方式、計算方式、存儲方式……伴隨著數字技術在出版、印刷領域的廣泛應用,傳統出版與傳統印刷已經出現并將繼續出現一系列不容逆轉的變化。
作者的寫作方式變了。數字時代前,作家的寫作有著大量的手稿,這也成為今天不少作家紀念館內的主要展示物。為了出版,編輯發稿后有大量工作需要印刷廠的工人來完成。計算機發明后,這一切變了,作者只須向出版社交付電子文檔,印刷廠的工作由以往的排版、修版、印刷變成了組版、印刷。在出現網絡文學與微博后,不用出版社加工即可付諸“出版”,供人們閱讀。
人們的閱讀習慣變了。電子閱讀器的出現,使得人們越來越多地選擇網上閱讀、手機閱讀。從網上看新聞放棄了新聞報;從網上看小說放棄了紙質圖書……統計數據顯示,現在的大學生對上網閱讀與傳統紙質書的喜愛度幾乎各半。
圖書的發行方式變了。書店原本是圖書實現銷售的重要環節,從實體書店了解圖書出版狀況、實現所需圖書的購買,但在當當網、京東網等一批網上書店出現后,成本偏高的實體書店銷售疲軟,從網上獲取圖書不僅便捷而且在價格上具有優勢,原有的書店不得不更多地從事文具或其他產品的銷售以維持生存。
其實,變是世間萬物生存之道;適者生存,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既然數字技術的出現已經對傳統出版業和傳統印刷業構成挑戰,那惟有出版社和印刷廠通過改變自身去適應數字技術帶來的這一切變化。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者擴大市場份額,被動跟隨者有可能被市場無情淘汰。
自2009年起,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財務司(后改由出版產業發展司)在每年發布的年度統計報告中就單列出數字出版的相關信息,2009年數字出版的總產值是799.4億元,而且號稱超過了傳統的書報刊出版產值,2011年這塊數據更是增至1051.8億元。但分析2009年的數據就可以發現,這塊構成中的相當部分產值并非傳統出版的轉移,而是由新興電子產業所帶來,排位前三的分別是:手機出版314億元、網絡游戲256.2億元、網絡廣告206.1億元,這三塊的產值占到數字出版總量的98%,而從傳統出版轉移過來的數字雜志只有6億元,顯得極為渺小。如此分析并非是抹煞數字出版取得的成績,僅是希望在看到長足進步的同時更多地看到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移的力度并不大,在知識產權保護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出版社還是把傳統出版的內容資源作為企業安身立命之本的時候,傳統出版業向數字出版方向轉移的步伐就不可能邁得很大。因此,我們也無需把這方面取得的成績描繪得令人眩目。
從數字解決方案組織得到的信息稱,2010年美國的數字印刷產值已經占到全部印刷產值的27%,但追問這27%產值的構成,一時卻難以給出明確的答案,有說是照片印放比重大,有說是直郵單據產值大,莫衷一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滿足個人愛好的圖書按需印刷應該占據著數字印刷的相當份額,在我國,這一領域的印刷量尚屬鳳毛麟角,卻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數字出版的量還相當有限。
與此相對應的倒是2010年我國圖書傳統印刷量達到71.4億冊,出現了自1999年以來的次年印量超70億冊(1999年為73.46億冊),當然,這一年全國新華書店及出版社自辦發行的庫存總量也從1999年的34.62億冊增至53億冊,總碼洋達到737.8億元。這一數據告訴我們,迄今為止傳統圖書印刷在出版領域依然唱著主角,數字印刷圖書至今還僅是用于打印送審稿、套裝書補缺及承印小印數的古籍書,傳統出版存在的預造貨庫存積壓問題依舊沒有得到絲毫改觀。
數字出版業的發展遲緩也理所當然地導致數字印刷量的增長緩慢,按上海市*發布的數據,2010年上海由數字印刷機印刷完成的產值5.95億元,2011年增至6.19億元,可以說無論是值(2400萬元)還是增速(4%)都顯得緩慢,這既同數字印刷產品現有成本偏高讓讀者敬而遠之有關,也同數字出版至今沒有形成便捷的運營網絡有關。
我國出版產業數字化改革還停留在一家一戶的低水平階段
數字出版發展緩慢的責任毫無疑問在于出版社,因為他們處于這一產業鏈的上游。知識分子云集的出版社當然了解數字出版的發展趨勢與其不可替代的優越性,但現實的利益與他們的能力使得數字出版依然停留在一家一戶的低水平上,大多在做的也就是將歷*已經出版的圖書進行數字化錄入。而且,每個出版集團幾乎都在自建數字印刷工廠,掌握著內容資源的出版社至今希冀把與數字出版相關聯的一切都捏在自己手上而不考慮走社會化道路,如何讓數字出版做到聯網運行似乎至今還沒有一個機構在加以考慮。這一思想認識無疑阻礙了數字出版在國內的發展。
數字出版的特點是按讀者需求就近印刷,要做到這一點,絕不是靠一家出版社或者一個出版集團的力量,而是必須利用社會上現有的數字印刷工廠,通過網絡連成一片,由內容供應商(出版社)、渠道供應商(網絡提供者)與印刷供應商共同來完成。
再則,數字出版的優勢是能夠根據讀者的需求,為讀者量身定制。比如,某位研究生為了書寫論文,希望有專業出版社為他提供一本專業圖書,反映一段時間來圍繞此項研究專題已經發表的新成果,如果能夠完成研究生的這一訴求,我們的出版業自然又大大前進了一步,但至今又有哪家出版社有如此可能呢?再退一步說,又有哪家出版社感到在走進數字出版時代后應該去做上述工作?可能至今還只能說沒有,我們的認識還沒有達到這一境界。既如此,我們又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我們應該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應該建設一個出版業的“中國銀聯”
“中國銀聯”不是銀行,是銀行間的一個交換平臺,他為銀行提供關聯服務,也從銀行得到回報。“中國銀聯”無疑是銀行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中國有著500多家出版社,是否也能建設一個類似于“中國銀聯”的“中國版聯”,他也不以自身組織出版為基本業務,而以為所有出版社提供數字出版的共享平臺為責任,同“銀聯”一樣,他的收入也不來自于自己面對社會的經營,而是因為為出版社的數字出版提供了平臺,完成了關聯業務,那出版社應該在自己的獲利中拿出一塊交納給這一平臺,當然,也由這一平臺完成對所有關聯企業的相應分配。
同組建“中國銀聯”一樣,組建“中國版聯”應該是由國家有關部門牽頭。因為,惟有他們才有可能著手去做這樣一件事關所有出版社的事情,任何一家具體的出版社或者出版集團都難有如此去凝聚如此多的出版機構。因為,組建這樣一個運營平臺,牽涉到各方的利益,需要部門協調,惟有國家有關部門才有如此。因為,組建平臺需要相應的資金,由政府先行出資待成熟后再逐漸償還比較容易走通。可以相信,這樣的事情做好了或許推進數字出版的前提也就有了,否則,更多的還是雷聲大雨點小,真正推進的成效并不明顯。
上述想法可能幼稚,但如果由此能夠引來更多的、實實在在有助于數字出版發展的金點子自然就更好。
一言以蔽之,數字技術的出現推動著社會的變化,順應發展潮流,主動推進數字出版是當代出版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能否做好這項工作,不僅關系到數字出版的發展,而且與數字印刷的發展緊密相連。我們為數字出版迄今已經取得的成績歡與鼓,我們更期待著中國數字出版事業的井噴,真正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貢獻出出版業的力量。
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百年紀念,特意向中華書局發去了賀信。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曾經說過:“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百年前的出版人尚且有如此認識,難道今天的出版人不應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些嗎?
數字技術稱得上是二十世紀的偉大發明,數字技術的出現改變了信息傳遞;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改變了生產方式、計算方式、存儲方式……伴隨著數字技術在出版、印刷領域的廣泛應用,傳統出版與傳統印刷已經出現并將繼續出現一系列不容逆轉的變化。
作者的寫作方式變了。數字時代前,作家的寫作有著大量的手稿,這也成為今天不少作家紀念館內的主要展示物。為了出版,編輯發稿后有大量工作需要印刷廠的工人來完成。計算機發明后,這一切變了,作者只須向出版社交付電子文檔,印刷廠的工作由以往的排版、修版、印刷變成了組版、印刷。在出現網絡文學與微博后,不用出版社加工即可付諸“出版”,供人們閱讀。
人們的閱讀習慣變了。電子閱讀器的出現,使得人們越來越多地選擇網上閱讀、手機閱讀。從網上看新聞放棄了新聞報;從網上看小說放棄了紙質圖書……統計數據顯示,現在的大學生對上網閱讀與傳統紙質書的喜愛度幾乎各半。
圖書的發行方式變了。書店原本是圖書實現銷售的重要環節,從實體書店了解圖書出版狀況、實現所需圖書的購買,但在當當網、京東網等一批網上書店出現后,成本偏高的實體書店銷售疲軟,從網上獲取圖書不僅便捷而且在價格上具有優勢,原有的書店不得不更多地從事文具或其他產品的銷售以維持生存。
其實,變是世間萬物生存之道;適者生存,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既然數字技術的出現已經對傳統出版業和傳統印刷業構成挑戰,那惟有出版社和印刷廠通過改變自身去適應數字技術帶來的這一切變化。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者擴大市場份額,被動跟隨者有可能被市場無情淘汰。
自2009年起,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財務司(后改由出版產業發展司)在每年發布的年度統計報告中就單列出數字出版的相關信息,2009年數字出版的總產值是799.4億元,而且號稱超過了傳統的書報刊出版產值,2011年這塊數據更是增至1051.8億元。但分析2009年的數據就可以發現,這塊構成中的相當部分產值并非傳統出版的轉移,而是由新興電子產業所帶來,排位前三的分別是:手機出版314億元、網絡游戲256.2億元、網絡廣告206.1億元,這三塊的產值占到數字出版總量的98%,而從傳統出版轉移過來的數字雜志只有6億元,顯得極為渺小。如此分析并非是抹煞數字出版取得的成績,僅是希望在看到長足進步的同時更多地看到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移的力度并不大,在知識產權保護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出版社還是把傳統出版的內容資源作為企業安身立命之本的時候,傳統出版業向數字出版方向轉移的步伐就不可能邁得很大。因此,我們也無需把這方面取得的成績描繪得令人眩目。
從數字解決方案組織得到的信息稱,2010年美國的數字印刷產值已經占到全部印刷產值的27%,但追問這27%產值的構成,一時卻難以給出明確的答案,有說是照片印放比重大,有說是直郵單據產值大,莫衷一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滿足個人愛好的圖書按需印刷應該占據著數字印刷的相當份額,在我國,這一領域的印刷量尚屬鳳毛麟角,卻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數字出版的量還相當有限。
與此相對應的倒是2010年我國圖書傳統印刷量達到71.4億冊,出現了自1999年以來的次年印量超70億冊(1999年為73.46億冊),當然,這一年全國新華書店及出版社自辦發行的庫存總量也從1999年的34.62億冊增至53億冊,總碼洋達到737.8億元。這一數據告訴我們,迄今為止傳統圖書印刷在出版領域依然唱著主角,數字印刷圖書至今還僅是用于打印送審稿、套裝書補缺及承印小印數的古籍書,傳統出版存在的預造貨庫存積壓問題依舊沒有得到絲毫改觀。
數字出版業的發展遲緩也理所當然地導致數字印刷量的增長緩慢,按上海市*發布的數據,2010年上海由數字印刷機印刷完成的產值5.95億元,2011年增至6.19億元,可以說無論是值(2400萬元)還是增速(4%)都顯得緩慢,這既同數字印刷產品現有成本偏高讓讀者敬而遠之有關,也同數字出版至今沒有形成便捷的運營網絡有關。
我國出版產業數字化改革還停留在一家一戶的低水平階段
數字出版發展緩慢的責任毫無疑問在于出版社,因為他們處于這一產業鏈的上游。知識分子云集的出版社當然了解數字出版的發展趨勢與其不可替代的優越性,但現實的利益與他們的能力使得數字出版依然停留在一家一戶的低水平上,大多在做的也就是將歷*已經出版的圖書進行數字化錄入。而且,每個出版集團幾乎都在自建數字印刷工廠,掌握著內容資源的出版社至今希冀把與數字出版相關聯的一切都捏在自己手上而不考慮走社會化道路,如何讓數字出版做到聯網運行似乎至今還沒有一個機構在加以考慮。這一思想認識無疑阻礙了數字出版在國內的發展。
數字出版的特點是按讀者需求就近印刷,要做到這一點,絕不是靠一家出版社或者一個出版集團的力量,而是必須利用社會上現有的數字印刷工廠,通過網絡連成一片,由內容供應商(出版社)、渠道供應商(網絡提供者)與印刷供應商共同來完成。
再則,數字出版的優勢是能夠根據讀者的需求,為讀者量身定制。比如,某位研究生為了書寫論文,希望有專業出版社為他提供一本專業圖書,反映一段時間來圍繞此項研究專題已經發表的新成果,如果能夠完成研究生的這一訴求,我們的出版業自然又大大前進了一步,但至今又有哪家出版社有如此可能呢?再退一步說,又有哪家出版社感到在走進數字出版時代后應該去做上述工作?可能至今還只能說沒有,我們的認識還沒有達到這一境界。既如此,我們又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我們應該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應該建設一個出版業的“中國銀聯”
“中國銀聯”不是銀行,是銀行間的一個交換平臺,他為銀行提供關聯服務,也從銀行得到回報。“中國銀聯”無疑是銀行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中國有著500多家出版社,是否也能建設一個類似于“中國銀聯”的“中國版聯”,他也不以自身組織出版為基本業務,而以為所有出版社提供數字出版的共享平臺為責任,同“銀聯”一樣,他的收入也不來自于自己面對社會的經營,而是因為為出版社的數字出版提供了平臺,完成了關聯業務,那出版社應該在自己的獲利中拿出一塊交納給這一平臺,當然,也由這一平臺完成對所有關聯企業的相應分配。
同組建“中國銀聯”一樣,組建“中國版聯”應該是由國家有關部門牽頭。因為,惟有他們才有可能著手去做這樣一件事關所有出版社的事情,任何一家具體的出版社或者出版集團都難有如此去凝聚如此多的出版機構。因為,組建這樣一個運營平臺,牽涉到各方的利益,需要部門協調,惟有國家有關部門才有如此。因為,組建平臺需要相應的資金,由政府先行出資待成熟后再逐漸償還比較容易走通。可以相信,這樣的事情做好了或許推進數字出版的前提也就有了,否則,更多的還是雷聲大雨點小,真正推進的成效并不明顯。
上述想法可能幼稚,但如果由此能夠引來更多的、實實在在有助于數字出版發展的金點子自然就更好。
一言以蔽之,數字技術的出現推動著社會的變化,順應發展潮流,主動推進數字出版是當代出版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能否做好這項工作,不僅關系到數字出版的發展,而且與數字印刷的發展緊密相連。我們為數字出版迄今已經取得的成績歡與鼓,我們更期待著中國數字出版事業的井噴,真正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貢獻出出版業的力量。
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百年紀念,特意向中華書局發去了賀信。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曾經說過:“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百年前的出版人尚且有如此認識,難道今天的出版人不應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些嗎?
版權與免責聲明:1.凡本網注明“來源:包裝印刷網”的所有作品,均為浙江興旺寶明通網絡有限公司-興旺寶合法擁有版權或有權使用的作品,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包裝印刷網”。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2.本網轉載并注明自其它來源(非包裝印刷網)的作品,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或和對其真實性負責,不承擔此類作品侵權行為的直接責任及連帶責任。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轉載時,必須保留本網注明的作品第一來源,并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 3.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周內與本網聯系,否則視為放棄相關權利。
相關新聞
-
12月5日,2015湖北文化產業合作洽談會在漢舉行,10個項目現場簽約。來自美國、日本等15個國家以及港澳臺地區的文化產業商務官員、公司高管100余人,與湖北文化企業代表聚集一堂、共謀商機。
- 2015-12-08 09:14:41
- 8141
-
- 2012-10-08 10:24:04
- 1294
-
- 2010-12-20 11:38:40
- 838




 直播回放
直播回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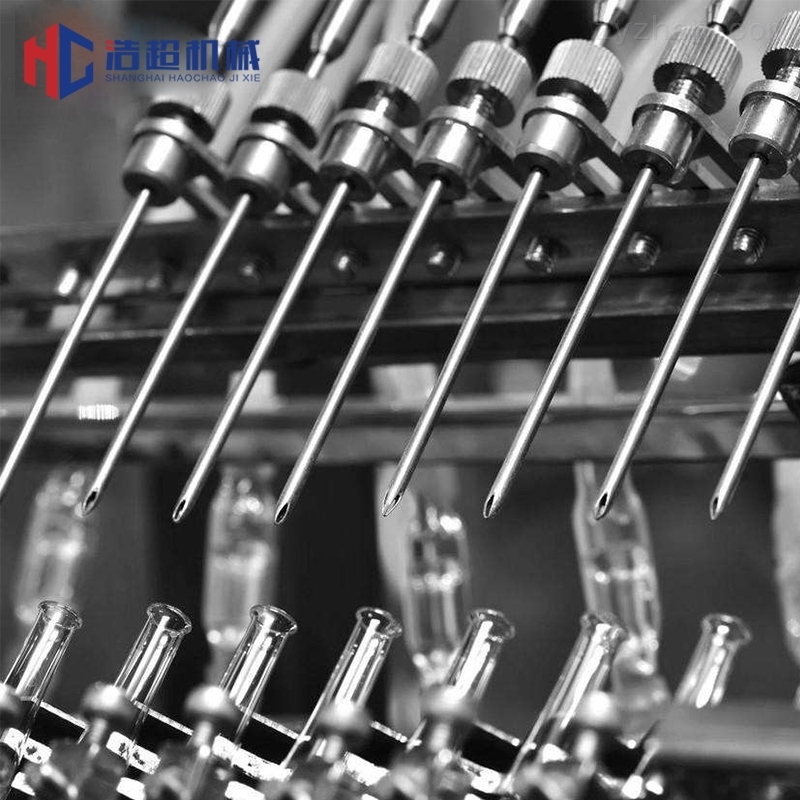 直播回放
直播回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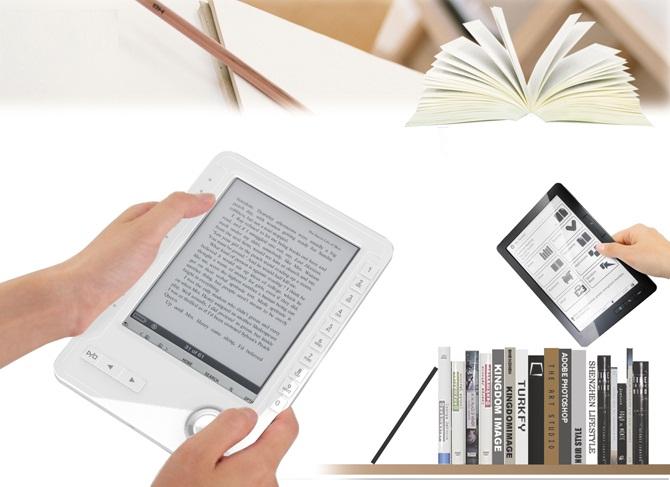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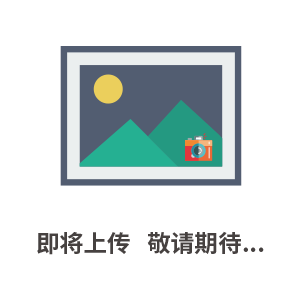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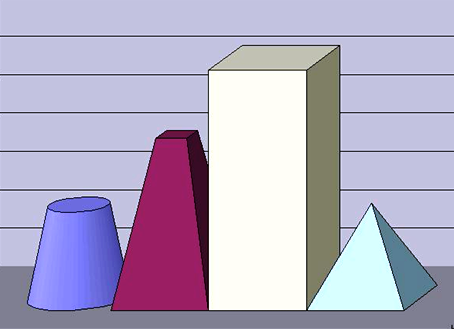

















昵稱 驗證碼 請輸入正確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與本站立場無關